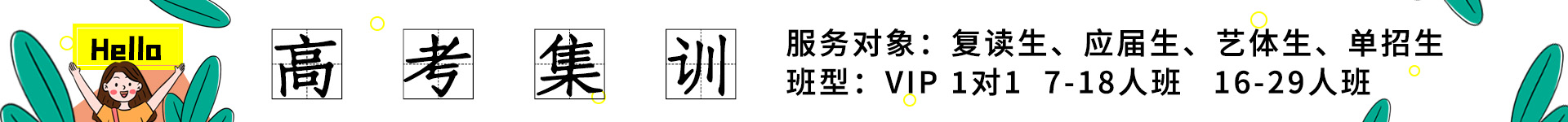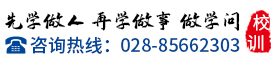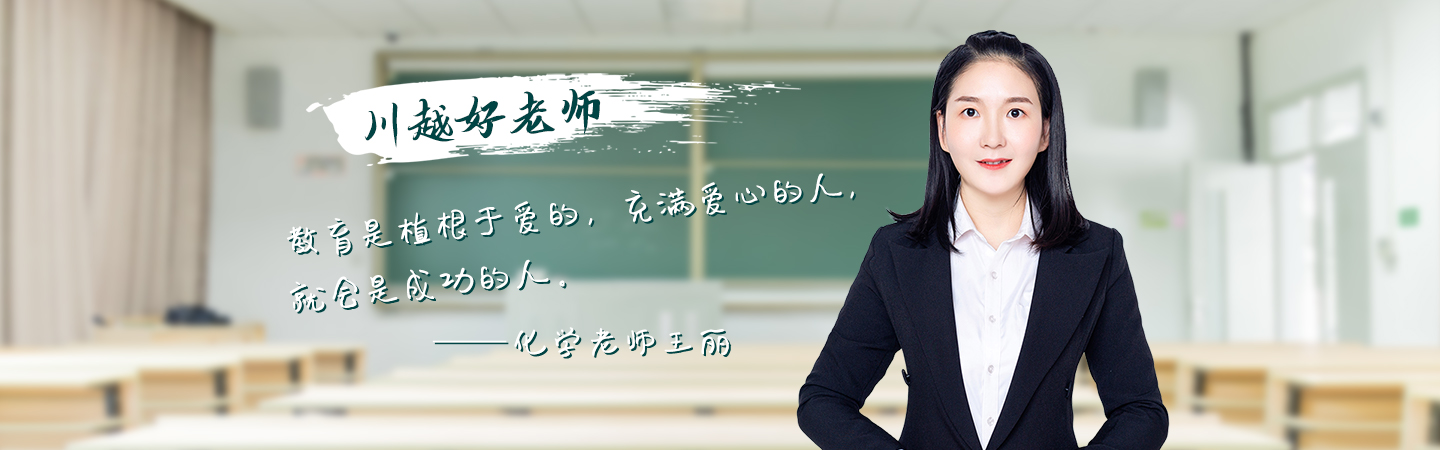
-
以學正風強根基 篤行致遠踐初心 2025-05-06
-
高校分類評價機制構建的重要經驗與關鍵要點 2025-04-10
-
三部門聯合發文:加強語言文字復合型人才培養 2025-04-01
11月29日上午,一張截圖在網上流傳,內容為饒毅實名舉報武漢大學醫學院李紅良教授、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化細胞所裴鋼院士、上海藥物所耿美玉研究員等3學者論文造假。饒毅在今年6月就任首都醫科大學校長,他還是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終身講席教授。
目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工作人員正在調查核實此事。
另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中國新聞周刊》已將上述截圖發給饒毅本人求證,饒毅回復稱:“沒有發出,有過草稿。”
舉報信:
《中國新聞周刊》將上述截圖發給饒毅本人求證。饒毅回復稱:“沒有發出,有過草稿。”
這封流傳的舉報信中提及的第一件事為李紅良被疑造假風波:“貴委應該有效、有膽魄地徹底調查武漢大學醫學院李紅良17年如一日明目張膽的造假。”
2018年1月,科學新媒體“知識分子”率先爆料武漢大學教授李紅良論文涉嫌造假一事。2017年,李紅良在影響因子為30的《自然·醫學》上發表了4篇文章,武漢大學“千人計劃”特聘專家霍文哲向《知識分子》舉報稱,其中兩篇論文涉嫌造假。饒毅是“知識分子”的三位創始人之一,并擔任其主編。
2018年1月29日,武漢大學官方微博發布了《關于李紅良團隊被舉報學術不端的調查意見》,認為李紅良團隊被舉報的相關內容不存在學術造假,但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存在個別疏漏。
據武漢大學官網信息,李紅良現任武大基礎醫學院院長、動物實驗中心主任,武漢大學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長、中南醫院醫學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
11月29日晚,回憶起當時的調查情況,兩院院士,時任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李德仁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稱,當時講過五句話:第一,武漢大學鼓勵教師從事原創性的,對人的健康有益的難題的研究。第二、研究中間要老老實實,精益求精,嚴謹,一絲不茍。第三、當時投訴李紅良的材料經過同行知名院士、專家做了兩次核查,所有的原始文件沒有發現造假性。他的文章發表確實有些疏漏。比如這個圖連兩邊(文章)都用過,互相沒有引證。第四,不要去用SCI篇數來論英雄、評職稱、當學者、戴帽子。“所謂SCI論文你比我多,你就當‘杰青’,我比他少就當不了。簡單的量化,評估是錯的,會助長年輕的學者急于求成。”第五,如果投訴的人說得不對要做檢討。“你投訴人家了,一分錢不花,網上折騰人家查了好幾年。如果投訴一個人投訴的不對,你要做自我批評。”當問及李紅良學術水平,李德仁表示,應該可以。“要不Nature Medicine他兩年怎么發四篇文章呢,(他)發過好文章。”
上述舉報信中提到的第二位當事人為中科院院士裴鋼。原文寫到:“貴委應該嚴肅調查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化細胞所研究院(編者注:應為“員”)裴鋼,于1999年,用貴委三項經費(39630130、39625015和39825110)支持其發表的論文(Ling et al.PANS96:7922-7927)。”
經記者查詢,該段文中提到的三串數字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資助的三個項目的批準號,其中可查到前兩個項目的負責人皆為裴鋼。據此判斷,這是一封擬發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舉報信。
該段提及的論文為裴鋼于1999年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PNAS)上,標題為《五跨膜結構域足以作為G蛋白偶聯受體:功能性五跨膜結構域趨化因子受體》,裴鋼為通訊作者,馬蘭為共同作者。裴鋼曾先后擔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同濟大學校長,1999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現為中國細胞生物學會理事長。2019年,裴鋼的妻子、復旦大學醫學院教授馬蘭也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饒毅舉報的第三篇論文,是今年9月發表在《Cell Research》上的,裴鋼為該雜志主編。論文題為《寡聚糖鈉鹽治療重塑腸道微生物群,抑制腸道細菌氨基酸型神經炎癥,抑制阿爾茨海默病的進展》。11月2日,被國家藥監局“有條件批準”的治療阿爾茲海默病新藥GV-971,商品名“九期一”,便是基于這篇文章所闡釋的作用機理。該藥物的主要發明者、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學術所長耿美玉系該文通訊作者。
在這篇論文中,耿美玉團隊提出了GV-971的作用機制:通過重塑腸道菌群平衡、降低外周相關代謝產物苯丙氨酸/異亮氨酸的積累,減輕腦內神經炎癥,進而改善認知障礙,達到治療AD的效果。“這篇文章,不造假是不可能的。”上述舉報信稱。
就這封舉報信的草稿為何會泄露、下一步如何處理等事宜,《中國新聞周刊》詢問饒毅,但未得到進一步回復。在這封舉報信落款“饒毅”的下方,括號中注明如下文字:代表個人、不代表任何單位。
29日,《北京青年報》記者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獲悉,該委目前正在調查核實此事。
截至發稿時,《中國新聞周刊》尚未得到裴鋼方面的回應。
1
三位被舉報的教授的公開信息
學術不端在全球是普遍現象,不惟中國獨有。但是,論學術不端的人數之多,涉及范圍之廣,不端比例之大,行為之猖獗,均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就在饒毅舉報之前的 11 月 14日,前斯坦福大學助理研究員 Elisabeth Bik 在 PubPeer 網站公開指出,現任南開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曹雪濤為通訊作者、共同通訊作者或合作者的多篇論文涉嫌“圖像不當復制”問題。
例如,天津市外國語學院文化學院副教授沈履偉抄襲案,武大周葉中涉嫌抄襲案等等。后來發現,在當下的中國學術界,各種學術不端的手法層出不窮,而且花樣翻新。
這些年來,行政指揮學術的現象愈演愈烈,各種考核、指標、課題等等,讓已經異化的學術體制進一步扭曲。雖然高等教育的質量仍在上升,但是,它上升的幅度和現狀,遠遠不能匹配相應的投入。為了應付各種考核和評職稱、跑課題,許多學者為了完成量化指標而疲于奔命,用在教學和研究上的時間和精力不得不減少。
當然,這不是學術造假的正當理由。對于學者而言,在科學和研究中保持誠實,是從業最基本的要求。而學術不端屢禁不絕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成本太低。在高等教育發達且制度健全的國家,學術不端者被發現之后,將會辭職或被開除,并且遭到學術界的共同抵制,這也意味著學術不端者以后再也找不到學術研究工作。在國內,這種現象卻很少見。而饒毅此次舉報引發如此重大的影響,原因之一是因為被舉報者身份屬于“重量級”:李紅良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創新領軍人才,現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裴鋼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同濟大學校長。
可以想見,如果李紅良、裴鋼這樣文明社會中的精英,如此重量級的學者涉嫌學術不端,它將造成怎樣的社會后果?
2
而背后的利益糾葛,也頗為震撼!
2019年11月2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了上海綠谷制藥有限公司治療阿爾茨海默病新藥——九期一(甘露特鈉,代號:GV-971)有條件臨床上市使用。
消息一出,媒體炸了鍋。
看看官方的報道:
甘露特鈉膠囊(商品名“九期一”,代號GV-971)由中國海洋大學、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和上海綠谷制藥有限公司聯合研發。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員領導研究團隊,堅持22年,克服重重困難,終于研制成功。
它作為中國原創、國際首個靶向腦-腸軸的阿爾茨海默病治療新藥,通過優先審評審批程序在中國大陸全球首次批準上市,填補了這一領域17年無新藥上市的空白。該藥的上市將為患者提供新的用藥選擇。
少數不明真相的傻b媒體甚至高喊:老年癡呆有救了!
阿爾茨海默病(AD,俗稱老年癡呆)主要表現為認知功能和行為障礙及精神異常等癥狀,是繼心腦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之后,老年人致殘、致死的第三大疾病。
全球至少有5000萬患者,我國超過1000萬。不幸罹患此病,不僅需要治療,而且需要健康人全職看護,看護人還極有可能被患者折磨導致抑郁,給患者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
更可怕的是,目前它是不治之癥。
發現阿爾茨海默病已經一百多年,發病原因卻知之甚少。全球用于臨床治療的藥物只有5種,效果都不明顯,等同于死馬當活馬醫。
過去20多年,全球各大制藥公司相繼投入超過六千億美元研發新藥,320多個進入臨床實驗的藥物已經宣告失敗。
近年來,數個新藥在大型Ⅲ期臨床實驗中遭遇失敗,更是讓科研界心灰意冷。
2018年1月,武田制藥宣布吡格列酮的阿爾茨海默病Ⅲ期臨床試驗失敗;輝瑞宣布放棄阿爾茨海默病領域的阿藥物研發;丹麥制藥公司Lundbeck的idalopirdine試驗性藥物未能阻止輕度及中度阿茲海默癥患者的認知能力下降,它曾被看作是治療阿茲海默癥最有希望的藥物之一;
2018年2月,默沙東宣布停止Verubecestat的臨床試驗;
2018年6月,禮來與阿斯利康聯合開發的lanabecestatⅢ期臨床中止;
2019年1月,羅氏宣布CrenezumabⅢ期臨床失敗。。。
唯一的曙光是今年10月23日,美國Biogen和日本Eisai生物技術公司宣布在研的阿爾茨海默病(AD)新藥有效,將于2020年初向FDA提出上市申請。他們的阿爾茨海默病新藥,III期臨床試驗先后持續了近四年,受試者超過3000名。
沒想到,被我們搶先批準上市了!
科研工作者誰不希望自己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早日變成產品造福人類呢?誰不希望能創造醫學史上的奇跡,名垂青史呢?!
他們的急迫心情,我們應當理解。哪怕是日后發現這是一出鬧劇,是不小心吹牛皮吹大了,我們也應當堅定支持他們。
有的人為名,有的人為利。
商人呂松濤,名下數十家公司,商業帝國生存必然要有利潤。最早是靈芝寶,不惜違法打廣告。其后是中藥注射液丹參多酚酸鹽,中藥保護品種,獨家生產銷售,暴利!
3
學術造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對于學術工作者來說,國家級基金和項目經費,是幫助其“脫貧”的最主要經濟來源——否則,就只有微薄的工資可拿。上文提到的一篇國家自然科技基金資助論文,獲得的資助為78萬元,那么即使扣除服務費30萬元,還有48萬元,再加上中介公司有“返點”,作者從國家手里賺到“50萬”并不太難。
饒毅舉報信中提到,今年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員作為通訊作者,發表的宣稱可治療小鼠阿爾茨海默癥論文存在造假情況。圖為耿美玉在綠谷研究院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造假的成本太過低廉,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計。一方面,國外SCI雜志幾乎靠中國人開飯,當然睜一眼閉一眼。如果不是這些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放水”,很難相信這些翻轉、復制的圖片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或發表。
有數據顯示,2018年9-11月,中國學者發文量排名前39位的雜志,在這三個月內總共刊發了約62508篇“中國論文”。如果有一部分選擇繳納版面費,則預估2019年全年中國學者也需向39個雜志繳納一大筆版面費。
中國國內對英文雜志、英文論文以及國外知名SCI雜志一向抱有崇敬心理,并沒有相應的核查機制。很多國內的學術出版物為了生存,都不得不和國外學術雜志做深度綁定;而且“研究成果”歸高校或研究院的行政人員統計,隔行如隔山,行政人員并沒有能力和資質審核這些自然科學領域的英文論文。
其實,嘲笑學術丑聞并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僅有嘲笑,挽回不了整個國家的慘重損失。可以說,學術研究是一切實踐的基礎,如果中國的學者沉迷于“操作”國家級基金和項目,如果中國的學術出版物被國外出版商牢牢掌握,如果中國的學術論文只能復制粘貼,那么中國失去的不僅僅是納稅人的巨額血汗錢,還有科學和技術的主動權和話語權。
更值得深思的是,國家級基金和資助項目,它的規章制度、項目評審,要能真正促進中國自然科學的研究和進步,而不能成為一些人牟利的溫床。
以發文件、喊口號、事后緊急調查的方式來處理學術不端事件,卻不指向這一“連環計”背后的產業鏈條,恐怕將孕育出越來越嚴重的“學術丑聞”。

【關注川越微信公眾號,了解更多】